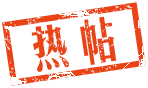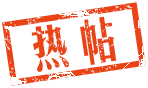|
|
先生品书,眼光开阔,堂庑甚大。宋元明刻之外,亦重视清刻并活字本。在跋嘉庆庚山草堂本《新安二江先生集》时说:“写刻精好,纸墨莹洁,开卷便有惊人之处。余尝谓清代刻本可上追赵宋,下俯朱明,正指此等书而言。”这不仅是卓识,也是确评。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日记:“忽发收集清代活字本之兴。”家书云:“我现在工作读书之外,经常到古玩铺古书铺一走。……书籍只限于清代活字本。以前藏书家皆轻视之,都不经意。一经收罗,趣味无穷。清代活字以木活字为多,我收到铜活字两种、泥活字两种,皆罕见之品也。”先生收清活字本,迄一九六六年五月“文革”开始时停止。五年中共得四百余种,皆捐赠天津图书馆。每年所得近百种,可见收书兴致不异昔时。先生余兴所至,兼及敦煌卷子、古玺印、书画、旧墨,并注意及王孝慈听藏的谭叫天戏目附题跋,可见兴趣之广。他又注意到清刻书所用的开化纸,这也是近代藏书家(如陶湘)所爱好而无人做深入探讨的。他的《温飞卿诗集笺注》跋,可看作最简净的开化纸源流考。
“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。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,其中有小开化较薄、白榜纸较厚等名目。陆容《菽园杂记》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,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,他省沿用之。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模印,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,纸薄而坚,色莹白,细腻腴润,有抚不留手之感,民间精本亦时用之。嘉道以后质渐差,流通渐稀,至于绝迹。此书是康熙时印本,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、乾隆两朝,非比较不能鉴别,辨其差异。偶有所会,聊记数语于此,他日当取清内府印本以证之。”
这是弢翁九十二岁时所写。有考证,有实验,是一篇精妙的小论文。从中可见他实事求是的态度,是做学问最难得的品格。弢翁其他考订版刻精粗、流传端绪的跋文,都可作如是观。
先生十分重视旧本刻工,曾辑有宋元刻工姓氏录,不只可为版本考订之助,更有重视刻字工人劳动之意,于《古文辞类纂》题识中说:“此本是清代乾嘉间金陵名工刘文奎、刘文楷兄弟所刻。寓流丽于方整之中,纸墨莹洁,传世甚稀,良可珍玩。清代乾嘉间金陵刻书习用刘氏方整之体,独穆大展则用楷书精刻,余所见有楷书刻《昭代词选》、摹元人书《两汉策要》,皆精妙绝伦。”他还考定大展生平身世,撰成小传。更值得纪念的是他对“文革”中上海朵云轩所刻的《稼轩长短句》的赏识。弢翁在一九八年家书中说:“昨见木刻《稼轩词》,名为仿元,实是自成一格,写刻殊佳。我眼馋,竟费廿八圆买了一部,惜纸不佳,如得佳纸佳墨,不在董刻之下也。”又于此书题识中说:“今见此书,秀丽精美,直欲上继康熙时扬州诗局之遗风,不禁惊喜。惜仍承袭轻视劳动人民之旧习,不著书于刻工姓名。”后来终于打听到此书刻成始末及书手、刻工姓名,著于跋尾。此书确是精美的佳刻,在十年动乱中刻成,真是奇迹。记得在北京饭店访谒弢翁时,他曾以此事见询,惜当时未见此书,无由应对,为可愧耳。
藏书者必广聚历代公私藏书书目,以为参考。旁及书影,先生于此事最所究心,所聚极繁富,尤重视宇内及日本景印本,每见必收。又以余力传刻旧本。新中国建立初期上海周宅藏书散出,于肆中收得先生所印宋刻《唐女郎鱼玄机诗》,珂罗版精印,大册毛订,纸墨精莹,真下真迹一等之书,荛翁藏书旧槚铭刻亦搨成附入,真是铭心佳品。又有董康影印如隐堂本《洛阳伽蓝记》,有我病手题,不知为先生别署也。为付厂估装成蝶装者。又尝得先生影印《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》,狭长大册,雅韵欲流。先生所印旧本之精美,往往如是。
先生定居天津,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,国难日亟,居华北者咸有国亡无日之感。其见于先生书跋中者如宋本《东观余论》跋:“癸酉正月,获见日本《文求堂书目》,著录宋元明本凡百余种,其中多沅丈旧藏,余尝于双鉴楼中得摩娑者,尤以北宋本《通典》、绍兴本《东观余论》为最罕秘,盖海内孤本也。《通典》索价一万五千圆,余力不能赎,乃以日金一千圆购此书归国,聊慰我抱残守缺之心。独念今者边氛益亟,日蹙地奚止百里,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中,余乃惜此故纸,不使沦于异域,书生之见亦浅矣,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。噫!”又跋明刻《虎钤经》云:“今日天下事益亟矣,纸上谈兵,空言何补,未尝不叹夫书生之迂见也。噫!”
两跋文情俱胜,纸上叹喟,其声可闻。爱国深情,寄于毫素。使善本不流入异域,其意甚壮,其情可哀。爱书与爱国,同是一事。先生之爱重中华文化实为爱祖国之体现,是最值得珍重的。
先生藏书事业,博大精深,非晚生末学所能窥其樊篱。不贤识小,辄以学习所得,成此笔记。幸不为先生所笑也。庚辰残腊书于来燕榭中。
|
|